去年元旦,我不無熱情地寫過一篇小文章《書業正在起變化》,為“一個充滿活力與希望的出版新時代”搖旗吶喊,引發業界共鳴。一年過去,上文所描述的一些書業發展現象與趨勢無疑更為明朗,對出版業的這些新趨勢我仍抱持樂觀態度。
同時,對當下中國書業發展的一些現狀,我也有著深深的困惑與憂慮。今天,我拋磚引玉,和業界朋友談談我對當今書業的困惑。歡迎拍磚。
出版大國的“小時代”
放在大歷史視野來看,我們當下所處的時代無疑堪稱“大時代”——國力蒸蒸日上,今年又恰逢“十三五”開局之年,而在“十三五”末,我們將迎來第一個“百年目標”。在此背景下,作為文化傳承重鎮的出版業自然也欣欣向榮——近幾年的年度產業分析報告無疑也印證了這一點。在有關機構2016年發布的“全球出版企業50強”排行榜上,有5家中國出版企業上榜;而且,中國也如愿以償地加入了國際出版商協會……毫無疑義,中國如今確實是出版大國。
然而出版大國卻完全走進了“小時代”。
過去十年,公認為是中國少兒出版的黃金十年。少兒圖書成為圖書出版各個門類中增長最為強勁的板塊,連續10年保持兩位數的高增長率。最近兩年,業界熱議少兒出版將迎來新的“黃金十年”。于是中國出版業出現了史無前例、全球罕見的少兒出版熱潮,所有出版社都齊刷刷地涌向少兒出版淘金——全國583家出版社沒有出版少兒讀物的已經屈指可數。2015年,全國出版少兒圖書3.7萬余種,品種增加4000余種。
前不久我聽說過一個非正式的數據,據說2016年全國的少兒圖書有望突破6萬種——對這個數據,我的直觀反應是難以相信的。但之所以傳出這樣一個數據,也說明了少兒出版的火熱之勢——不管有沒有條件,全國出版商正以更高漲的熱情義無反顧地撲向少兒出版。我還聽說過一個非正式數據,據說我國現在引進版圖書80%以上的品種都是少兒圖書——對這個數據,我的直觀反應仍然是難以相信,但這同樣說明了少兒出版熱究竟到了怎樣的程度。
全國出版人都來搞少兒出版,按理少兒出版的水平該達到相當的高度了吧?然而也未必。全國在少兒圖書上爆發出的各種質量問題(此處略去1000字,業界朋友自行補充)我就不多說了。
通過《出版商務周報》做的“低水平重復出版”專題相關文章,我悲哀地發現:少兒出版正成為全國出版人“比傻、比爛”的舞臺。少兒出版成為低水平重復出版最嚴重的領域,全國重復出版版本最多的圖書前幾百名的品種清一色的全是少兒讀物。少兒出版成了全國出版人心目中最不需要創造力最不需要專業精神的出版門類,大家都堅信一點:“那么爛的版本都能賣,我這一版應該不會是最差的吧。”出版人不再熱衷于創造,所追求的只是不要成為最差的那一個。大勢如此,少兒出版還能迎來新的“黃金十年”嗎?
而事實業已雄辯地證明了我的擔憂絕非杞人憂天。2016年,我們出版了那么多少兒圖書,真正讓大家感覺眼前一亮的好書有多少?業界討論說,2016年是出版業的“小年”,這在少兒出版上反映最為直觀——總體而言,原創乏力,亮點不多;業界的主要精力都在炒冷飯。對此,各大書店的暢銷榜也是明證——年度暢銷榜上的產品,有幾個是當年的新品?【需要補充一句的是,少兒原創繪本這兩年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水平大幅提升,可圈可點。向踏踏實實做優質原創的出版人致敬!】
一葉知秋。少兒出版如此,其他出版門類又能比少兒出版好到哪兒去呢?“出版小年”不單單是少兒出版,而是整個中國出版業的“小年”。
圖書營銷的“囚徒困境”
過去這兩三年,出版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各種新玩法層出不窮,驅動著出版業升級創新——而業界普遍認為,出版業的這些變化,本質上是渠道變革與營銷創新倒逼上游的結果。
過去兩三年,出版業危機感最重的大概是營銷策劃團隊,同時出版業最富創造力、最具爆發潛力的也是營銷策劃團隊。
在實體書店渠道,花樣百出的進校園活動、門店營銷策劃持續推出;更重要的是,各種前所未聞的營銷新玩法不斷改寫人們的認知,為業界創造出一個又一個的驚喜——眾籌出版、新媒體社群營銷、自營電商、跨界合作……今天跟眾籌網設計一個項目的眾籌方案,明天去羅輯思維搞個新品封閉銷售,后天搞一場微信群新書發布會……各種營銷新玩法為出版業擴充了新渠道,帶來一個又一個增量。一大撥出版營銷人,天天像打了雞血一樣,不斷琢磨,不斷嘗試,興高采烈地書寫著新的傳奇。
然而,2016年所有曾經的新玩法都成了套路,大V店、羅輯思維、年糕媽媽……都成了成熟的新興“傳統渠道”,出版營銷創新陷于停滯狀態——圖書營銷的實質歸結為一句話“線下搶書架,線上搶流量”,出版營銷人陷入無盡的焦慮與疲憊狀態。
線下怎么搶書架?不外乎搞講座、搞簽售、講故事、進校園……如果產品不夠有營銷點,這些都搞不動怎么辦?最直接的就是降供貨折扣,或者搞返點促銷,或者美其名曰搞創意陳列大賽,搞買贈,搞限時促銷……這些手法,對書店而言有多少創新嗎?真談不上。最后拼來拼去,主要還是拼和書店的人脈關系及明里暗里對書店的利益輸送情況。發行人心里的苦,怎一個累字了得!
然而,線上營銷并不比線下好搞。新媒體營銷編輯天天混跡各微信群,發紅包求轉發微信文章,紅包發出不少,閱讀量沒漲幾個,心頭滴血;或者天天腆著臉跟各路微信大號套近乎,求發文章,求合作——好不容易談成一單合作,往往也是靠狠讓折扣——常常還要自己承擔物流,最后吧啦吧啦一算,幾乎不掙什么錢。自我安慰,反正這是做的增量,攤薄成本,還能擴大影響。好多出版社發現,搞社群營銷累成狗,效果沒法預期,又不能放棄不做,痛苦不堪,最后發現線上營銷靠譜的還是幾大圖書電商和天貓店。
然而圖書電商的營銷體系和規則徹底給中國出版人玩壞了——要想爭取好位置,限時獨家是必須的;要想賣起來,買榜也是必由之路,常常吭哧吭哧準備幾百個賬號,沒白天沒黑夜地自己買自己的書;然后就是無窮無盡的各種返點促銷……背地里對渠道商怨聲載道,又天天腆著臉求對方給機會被宰割——線上圖書營銷就進入了這樣的怪圈。
圖書營銷就這樣陷入了套路,創新乏力,焦慮而疲憊!
出版主力的邊緣化
不僅圖書出版創新乏力,圖書營銷創新限于停滯,更重要的是,整個出版業——尤其是傳統出版業創新精神不足——行業的熱鬧與焦點現在都圍繞著政策與政府在轉,而沒有致力于踏踏實實推進業務創新。
當然,我這觀點可能有些狹隘——過于站在傳統出版人的視角看問題。如果把眼界放得更開闊一些,按我們新聞出版業的統計口徑,連搞網絡游戲的都算是在做出版——這樣看,出版業還是充滿活力,創新多多,生機勃勃的。
從廣義出版業的角度來說,最近一年出版業的最大亮點無疑是知識付費經濟的崛起。先是有分答的一夜爆紅;2016年6月,經過多年積累的喜馬拉雅FM推出付費音頻節目,一炮打響,快速攻城略地,在12月3日,喜馬拉雅以一己之力生造出一個“123知識節”,付費音頻節目一天銷售突破5000萬元,震動全國知識界;而嘗到賣書甜頭的羅輯思維也推出了自己的付費內容銷售平臺得到,短短半年,得到平臺上李笑來的《通往財富自由之路》專欄銷售突破2000萬元,多款產品銷售收入超過千萬……
毋庸置疑,分答、喜馬拉雅FM、得到等都是典型意義上的現代出版商。他們的創新,他們的表現都堪稱驚艷。
然而,這和我們傳統出版人、傳統出版企業又有什么關系呢?
在出版新經濟中,傳統出版企業、傳統出版人基本上是缺位的。當然,這種情況也不是這兩年才出現的情況。事實上,過去多少年出版新經濟就一直呈現這種態勢。比如,在數字閱讀領域,排名前列的閱文集團、掌閱等無一例外都沒有傳統出版的基因。
在圖書電商中,做出版出身的當當曾經一枝獨秀,引領中國的圖書電商。但是很遺憾,當當并沒有創造更多的驚喜,業界熱議,京東圖書整體超越當當已經為期不遠了。當當在電商中早已微不足道,現在居然在自己安身立命的圖書業務上也江河日下,風光不再。這不得不令人唏噓感慨,這恐怕和當當純粹的傳統出版基因不無關系……而在在線教育與教育信息化領域,數字閱讀領域的格局幾乎同樣呈現。傳統的教育出版社大多還停留在做多媒體數字教材、簡單的題庫產品層面,業界做得風生水起、不斷攻城略地的在線教育明星公司大多都是純粹的互聯網科技公司出身……
同時,各大出版上市公司的財報也顯示,除了傳統圖書出版發行業務,各大公司雖然在新業態上進行了諸多布局與探索嘗試,但這些公司的新業態收入很大程度上和出版業沒多大關系。以“內容+”為核心的出版新經濟在各大上市公司的收入結構中微乎其微。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在龐大的出版新經濟中,傳統出版的主力軍完全邊緣化了,出版業的融合發展,傳統出版機構幾乎完全處于被融合的地位。如此以來,不論出版新經濟發展多么迅猛,傳統出版機構、傳統出版人的未來又在哪里?
大時代呼喚出版大家
為什么會是這樣?恐怕關鍵還是出在人身上。
出版行業雖然古老,但它本質上永遠是青春的——因為出版是以創意為核心的產業。回顧古今中外,出版業的黃金時代無不是群星燦爛的文化、科技、藝術大發展的時代——而大量最優秀的學者、專家、作家都長期活躍在出版一線。
回過頭來看,上世紀八十年代也堪稱我國現代出版史上的一個黃金時代。當時在各行業中,出版業無疑是最具人才競爭力的行業之一。當時出版社引進的新人,幾乎清一色全是重點大學的高材生。而且,當時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出版業的大量編輯出身顯赫——要么父輩是著名作家學者,要么父輩身處省部級、廳局級高位。也就是說,當時進入出版業的要么有深厚的家學淵源,要么是時代的驕子,出版業吸納了一大撥社會精英。
但反觀當下,我們這個時代的出版業人力資源處于怎樣窘迫的處境?別說學養出眾的官二代鮮有選擇出版業的,就是重點大學的高材生也沒幾個選擇出版業了,出版業吸納的基本上是其他行業淘汰的人才。這就是現實。
再看如今各出版機構的領導人才,雖然也不乏優秀的,但能稱得上出版家的卻不多,出版大家則更是鳳毛麟角。
民營出版企業受限于身份,沒名沒分,能在這個行業里沉淀下來的,大多都是精明的商人——談什么出版情懷與文化理想?賺錢是第一位的。
而國有出版機構,現在普遍實行領導任期制,三年一換屆。在此背景下,大多數國有出版企業的領導并不是以“出版家”為自我期許——這對他們沒有誘惑力。說句不中聽的,雖然大多數國有出版機構都轉企了,但領導人普遍還是一副“做官”心態——要么想辦法保住位子,要么爭取謀求個更好的位子。于是,出版社領導追求的大多都是短期業績,打算長期扎根在出版社、一輩子踏踏實實做出版的反而成了我們這個行業的“稀有動物”。
前不久聽一位業界前輩談起國外的一家出版機構。這家機構在幾十年前啟動一個大型的出版項目,前后歷經了好幾任總編輯、幾十年才把這個出版項目搞成功。而啟動這個項目的總編輯坦承,他根本沒指望這個項目在他任上、甚至在他有生之年搞成功。為什么會這樣?因為他是在按出版規律做事,他對自己有著“出版家”的自我期許。這樣的事,在我國當今的出版業恐怕很難想象。
……
今天,我們走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征程上。“中國夢”不僅需要經濟、軍事、科技的支撐,更需要文化支撐——傳承文化、傳播文明,出版是關鍵的一環。但反觀今日中國書業之現狀,作為這個行業微末的一份子,我心彷徨。于是,把困擾我的幾個問題羅列出來,就教于方家。
在走向出版強國的路上,“革命”尚未成功,我輩仍需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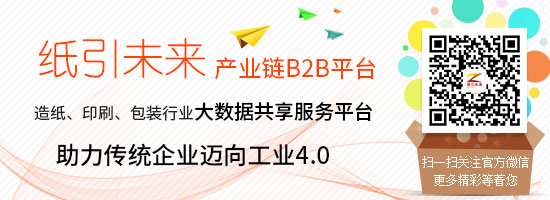
【免責聲明】
1、紙引未來發布此信息目的在于傳播更多信息,與本平臺網站立場無關。
2、紙引未來不保證該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文字、數據及圖表)全部或者部分內容的準確性、真實性、完整性、有效性、及時性、原創性等。
3、如有侵權請直接與作者聯系或書面發函至本公司轉達,及時給予刪除等處理。
- 下一篇:7月23日廣州市場鍍鉻板卷最新指導報價
- 上一篇:暫無
?
?
共0條 [查看全部] 相關評論
?
推薦圖文
推薦資訊
點擊排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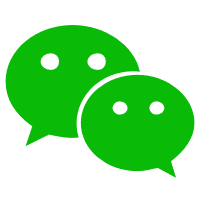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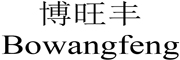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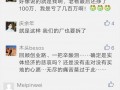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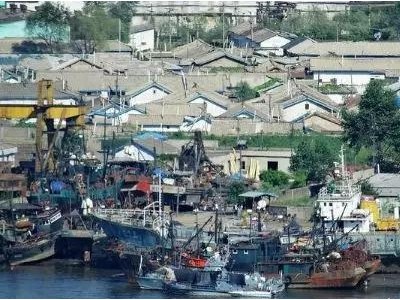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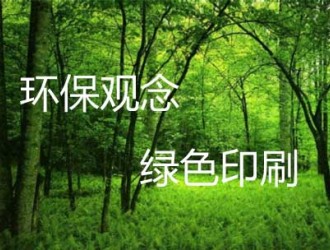


 紙友
紙友
 行情
行情
 訂單
訂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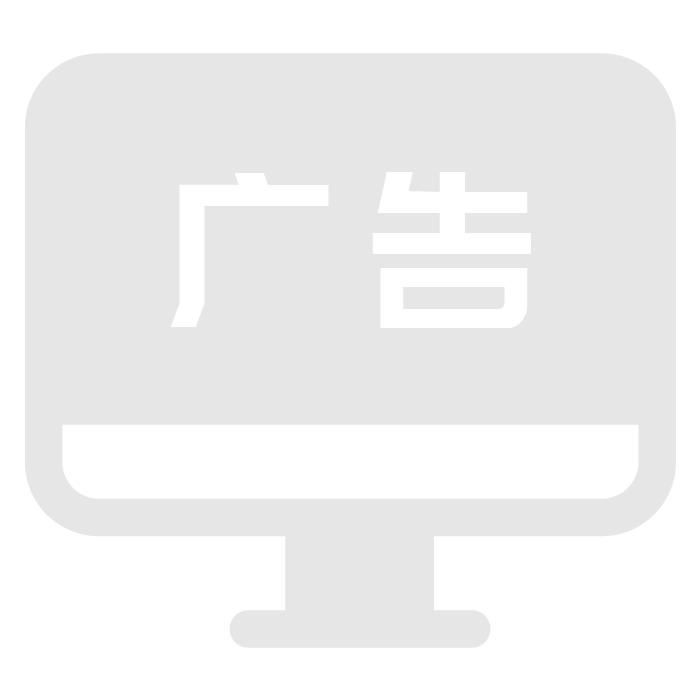 廣告
廣告
 找貨
找貨
 簽到
簽到

 關注
關注
 客服
客服 TOP
T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