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紀90年代李東方在工作的敦煌洞窟里留影
故事的主人公原名叫東方木子,后來改為李東方,現在是東方寶笈文化傳播公司總經理。但改來改去還是帶有“東方”二字,冥冥之中似乎有種力量決定了她注定要作為珂羅版這種西方技術的東方代表而揚名于世。2015年,李東方復制的《千手觀音圖》榮獲中華印制大獎金獎。

李東方用珂羅版技術復制的敦煌壁畫《美人菩薩圖》
讓世界見識了中國珂羅版
珂羅版是一項誕生于西方的印刷技術,19世紀末傳入到中國后,國內的珂羅版一直獨立發展,與西方沒有交流。一直到2013年法蘭克福書展上,德國珂羅版協會的專家看到李東方制作的中國書畫作品后,不僅承認這是真正的珂羅版,而且認為是非常高明的珂羅版制品。
通過與李東方的互動,德國珂羅版界全面了解了中國珂羅版發展的歷史和現狀,后來他們在為珂羅版申請世界非物質遺產的申報材料時特別加上了中國珂羅版的發展成就,以此證明珂羅版這種技術不僅是西方的,更是世界的。
從17歲在文物出版社印刷廠初識珂羅版,李東方在這個相對偏僻的領域里腳踏實地奮斗了40多年,其間雖然中國珂羅版事業歷經波折,幾起幾落,但她始終初心不改,終于成為中國珂羅版第三代傳人中的佼佼者。
把敦煌壁畫定格在90年代
從1984年開始,李東方兩次進入敦煌,陸續用了10多年的時間復制了大量的敦煌壁畫,為敦煌文化的保護貢獻了自己的力量,同時自己也通過對敦煌壁畫的復制,令技藝得到了升華。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李東方的技術水平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當時她在文物出版社印刷廠復制吳作人先生的《駱駝》,連吳老自己也辨認不出是不是真跡。但在輝煌的敦煌壁畫面前,李東方原有的技術積累不夠用了。常年的風化作用令壁畫表面大都斑駁破敗,顏色層次非常復雜,既有繪畫顏料的顏色,也有墻的顏色,泥土的顏色,這種情況以前還沒有遇到過。
敦煌研究院的領導對李東方的工作非常支持,把一些從未對外開放過的洞窟都對她開放了。從1996年~2006年的10年時間里,她每年4月~10月就是在這些黑暗的洞窟里度過,一點點研究,一點點嘗試,逐步摸索出一套適合的復制方案。她還記得,當她把局部原大的“反彈琵琶”貼在墻上與原畫融為一體的時候,許多老專家們都跳躍起來說:“逼真,傳神!”
在敦煌的那些年,李東方一共復制了300多平方米的壁畫,有的是局部放大的,有的是整體復制的,其中最令她滿意同時挑戰也最大的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該作品采用10塊版拼接而成,這也是世界上目前采用珂羅版技術制作面積最大的畫作。李東方在制作這幅畫的時候沒有采用傳統的幾何拼接法,而是泥巴拼泥巴,泥土色拼泥土色,墻皮色拼墻皮色,線條拼線條,顏色拼顏色,這在珂羅版技術上是一種突破。在2015年的中華印制大獎中,這幅畫也被評為藝術品復制金獎。
工匠精神三要素
有人說,李東方是印刷行業中工匠精神的代表。不久前共青團中央有關單位還特別制作了名為《李東方的“工匠精神”》的視頻節目,但對于什么是工匠精神,李東方坦言還沒有系統思考過,但她卻知道做一個合格的珂羅版技師,應該具備怎樣的品質。
首先是有恒。李東方曾經說,自己一輩子就做了珂羅版一項工作,整天琢磨的就是怎么樣把珂羅版復制得跟原件一模一樣,沒有想過別的,“說實話是愛一輩子,恨一輩子,怨一輩子,還是沒離開這一輩子”。
其次是悟道。現在李東方帶徒弟,常常教導他們要有悟性。她說,珂羅版雖然是一種技藝,但要以技悟道。“悟道”的程度如何,直接影響著作品的最終呈現效果。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要認真。李東方要求制版工比尺子畫線時不能畫在尺子的陰影里,因為這樣會有一個頭發絲的誤差,如果正好這條線就是人物的頭發,那么在套印時效果就會發虛,也就不可能實現逼真還原的效果了。“一絲不茍對別人來說就是一句成語,對珂羅版工人而言則是工作中的基本要求。”李東方說。
“做珂羅版臨制,最關鍵的因素在于人。100多年來,從事過這項工作的也就百來號人。如果現在不給他們打好基礎,將來誰來把這份事業延續下去?”現在李東方希望與有關單位共同辦一個珂羅版技術傳承班,把自己的技藝無保留地傳給下一代,并希望中國珂羅版能作為獨立項目成功申請世界非物質遺產,讓珂羅版的東方之花永遠盛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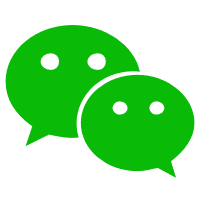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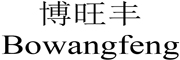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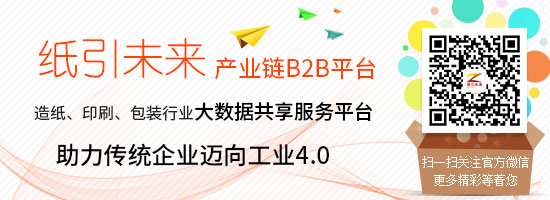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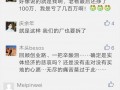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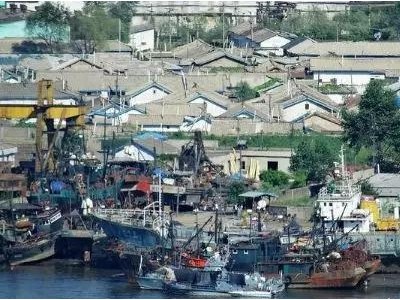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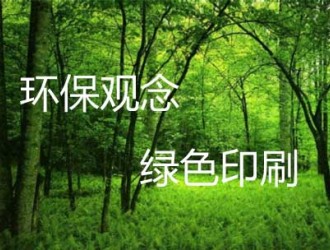


 紙友
紙友
 行情
行情
 訂單
訂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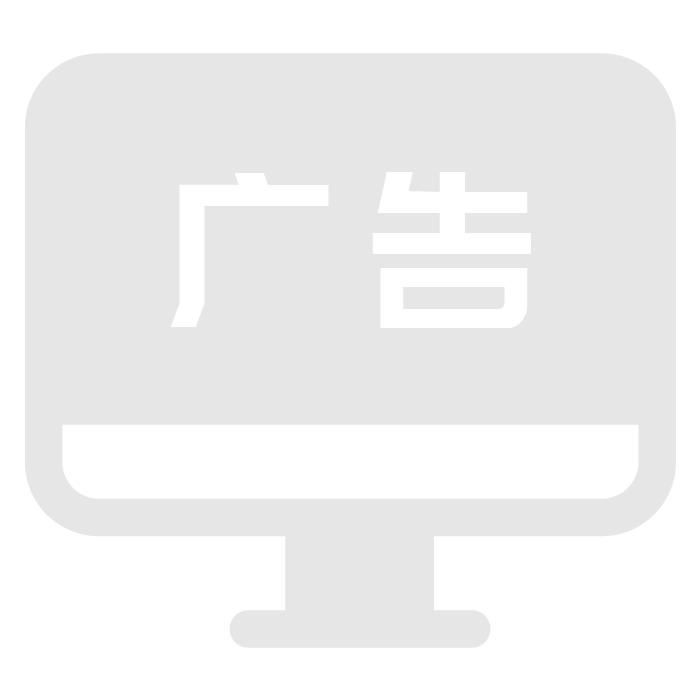 廣告
廣告
 找貨
找貨
 簽到
簽到

 關注
關注
 客服
客服 TOP
TOP

